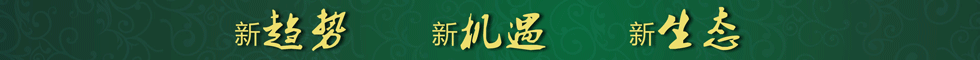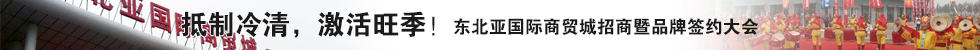[ 今年10月上海市社工委組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,有眾多鎮政府代表和社會組織出席。呂朝回憶,這個會類似于“集體招投標”,已經有一些鎮政府表示感興趣 ]
“政府只是造好房后移交給我們管理,居民從哪里來都跟我們沒關系。”浦東航頭鎮鶴沙航城社區黨委書記張鴻這樣理解“大居”,“在不變動鎮里人事編制的基礎上,突然多了1.5萬市里來的居民需要我們管理。”
2003年以來,上海開始組織實施大型居住社區建設(下稱“大居”),經過四輪選址,目前上海市有大型居住社區46個。而根據上海市建交委發布的信息,其中正在推進配套建設的大型保障房基地為21個。
比配套設施更不易處理的,是這些新興的“大居”里的公共服務和社區管理問題,《第一財經日報》記者了解到,為了彌補社區公共服務的不足,上海一些社區已開始試水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。
同步交付最困難
3年前的今天,航頭鎮鶴馳路還是一片稻田,而今路旁已是一片保障房,名為鶴沙航城社區。這里位于浦東最西南角,與奉賢、閔行接壤,申嘉湖高速南端,距東海僅半小時車程。
航頭作為浦東五大保障房大型居住區基地之一,將于2015年建成5.03萬平方公里的大型居住區,預計導入15萬人口。而浦東由于土地相對廣闊,承擔了上海市大居規劃總量的三分之一。
在2年的密集入住、導入1.5萬人口后,航頭大居居民的“排異反應”開始顯現。沒有大型醫院,就醫就必須坐車,而地鐵尚未開通,社區內僅有一處公交站點。
航頭社區中心主任胡德明告訴本報記者:“對于農村人來說,步行10分鐘以上到車站根本不是問題;而對于城里人來說,這就是問題。”胡曾經接到一位老人的投訴,對方稱車站太遠,“不習慣”。
而社區內一所全新的公立幼兒園,本是為解決居住區內動遷居民的子女教育問題,現在又因居住區入住率低,或學齡銜接不上等問題,而向農民工子女開放。
上海市房管局住宅建設發展中心(下稱“住宅中心”)承擔了上海市大型居住基地的中期推進和建設職務,該中心副主任匡韋仁告訴本報記者,在未經開發的鄉鎮,配套相對滯后于房屋建設是客觀規律,因為社區成熟有一個周期,因此大多數大居都無可避免于滯后的配套。
“建設中對于住宅和配套的關系有四同步要求,同步規劃、同步設計、同步建設和同步交付。同步交付最易出現問題,所謂的滯后也一般出現在這個環節上。”匡韋仁解釋說,第一,鄉鎮不會主動投資去造;第二,市政設施和公共建設又具靈活可調性,市規土局在項目的前期規劃上一般都是遠期規劃,一般不會先行建造;第三,在還未入住、沒有市場需求的情況下,如果先行導入設施,可能導致商業蕭條。
“政府只能想辦法相對縮短周期,但客觀規律不能改變。所以現在提出要保證基本配置,那就是起碼要有菜場、藥房、銀行等。”匡韋仁說。
城里人的管理成本
而在張鴻的感受里,公交車站都還是小問題,目前他最擔心的是怎樣解決逐漸增多的就業問題,“這不是一個農業鎮政府能夠解決得了的。”
“比如有的人以前是在市里做‘黃牛’的,而在鎮里又不可能去造一個體育場。”張鴻說,這種情況下,因為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,經適房違規商用屢禁不止。
胡德明則打了個比方,“航頭鎮常住人口6萬人,將管理將來新導入的15萬人,怎么管得了?”目前按政策,導入區將按照每年新交付面積得到300元/平方米的財政補助,名義為“管理費”。 而胡擔心的是,當交付完成的一天到來,也就意味著撥款結束。
在以面積掛鉤實行轉移支付之前,上海市對大居社區管理等公共支出,根據異地安置人口數量標準。經“每年核定,一次補貼”的原則實施專項轉移支付,資金由人口導出區財政承擔。后因人口流動不穩定,一些導入區提出意見,改為按面積數核定。
而“導入區”政府或“大居”管理者并不會滿足,并仍會反映“十補九不足”。“大多都要求建立長效機制,但這是不可能的。對多數鎮政府來說,都是錢到哪一步,他們就做到哪一步。”匡韋仁說。
“即使是按照農民的管法,都有管理成本,而城里人的管理成本肯定比農民高。”胡德明說。據了解,未來航頭將新增60個警察編制,而除此之外,在社區管理方面并沒有新增編制。
同樣的問題,在上海46個大居中均有顯現。據媒體公開報道,在松江區泗涇鎮保障房基地,個別小區八成以上居民為60歲以上老人。 “大居”低收入群體與老年人群集聚的情況已經影響到了物業的正常運轉,物業費繳納比例長期在三四成左右,虧損的物業要么退出,要么靠政府補貼維持低質服務。
截至2012年底,閔行區“大居”建設的資金缺口高達22億元。據閔行區財政局測算,每導入1名居民,區公共支出每年就將增加7400元。同時,公建配套項目的建設標準與居民的各項保障水平還在逐年提高。
閔行區浦江鎮曾測算,對大型居住區的投入涉及市政管理、社區管理、社會保障、社會救助、新居委會籌建、協管人員經費、社區活動經費、物業管理補貼等多項內容。按“大居”現有規模,政府每年需投入近1000萬元,而隨著更多基地建成和人口導入,投入費用將成倍增加。
匡韋仁表示,大居的管理按階段可分為前期、中期和后期,“最困難的就在于后期的公共管理”。
“那些居民除了在市里居住困難,其他的所有都可能是方便的。而現在導出后除了居住開心,可能其他都不方便,所以居住改善所帶來的高興可能只維持了1個星期。”匡韋仁說。
上海2012年開工、籌措保障房16.58萬套,今年則為10.5萬套,匡韋仁說,這并非意味著上海有意減緩保障房。“一是國家指標在降低;二是市場需求在長期中有所釋放,但保障房是一大門類,需求會在其下各品種間流動。”
“鎮管社區”試驗田
上海建保障房“大居”可追溯至1996年住房制度改革,上海開始探索商品房和保障房雙軌機制,于1997年推出全市首批平價房。翌年,上海成立經適房發展中心。
2009年,上海加快規劃大型居住社區基地,2009年和2010年成為基地規劃的濫觴期,分別出爐15個和23個基地。
在房價回升的“十二五”初期,國家在2011年年初拋出1000萬套保障房指標,市政府寄望于保障房平抑上海房價,促進上海樓市健康、穩定發展,由此,分層次、多渠道、成系統地完善住房保障體系。
上海市在2011年,曾有市委、市發改委、市社工委三股力量介入到“鎮管社區”模式的調研中,探索這個模式是否能常規化復制下去,以及是否有必要成立街道。如果按5萬人成立街道的標準,很多大型居住區無疑符合,但受限于街道與鎮政府的平級關系,最終沒有成立街道。
2011年11月舉行的上海市社區工作會議上,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殷一璀對《關于加強新形勢下社區建設的若干意見(討論稿)》(該文件于當年通過)做了說明,該討論稿明確表示,要探索推進“鎮管社區”體制改革,推進城鄉接合部地區和大型居住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。發揮鎮建制的優勢,一般不另設街道辦事處,由鎮政府承擔起社區管理的任務。
為了彌補鎮政府在社區公共服務上的不足,航頭鎮鶴沙航城社區中心開始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。通過去年9月的網上招標,目前有4家社會組織進駐社區中心,在并不豪華的小樓里,它們各自派駐一兩個人辦公。
對于張鴻和胡德明來說,他們認為請這些社會組織來一起辦公,恰恰也能讓自己“像學生一樣向他們學”。
“政府購買服務”在浦東新區已實行多年,據可接觸最早資料來看,2006年,該區有關部門委托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項目的資金近6000萬元,并專門組織8個政府部門和13個社會組織集中簽訂購買服務合同。
浦東新區政府采購辦公室一位周姓主任告訴本報記者,“政府購買服務”無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,均由各級政府自行委托、購買、評定。
上海市發改委一份文件稱:“浦東12個街道辦事處不再直接從事招商引資活動,把主要精力放在社區就業、養老服務等職能上,并將社會和社區可以承擔的一些公共職能,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委托給社會組織和社工機構承擔。”
在浦東,三林鎮世博家園大型居住區在2007年便參與了購買服務行動。該大居是上海世博會召開前的配套工程之一,安置了世博園園址上的動遷居民。近年來它的發展進程逐漸成為上海市各個“大居”中的首魁,社區建設與公共服務堪比成熟社區。
浦東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(下稱“恩派”)是世博家園最早的服務提供者,該中心負責人呂朝認為,社會組織進入社區的功能有二:提供公共服務和促進社區治理,而作為市郊剛落戶的大居“亟待重建社區”。
2007年,呂朝首次和三林鎮政府談合作時,他記得該社區空蕩一片。當時的三林鎮并沒有購買服務的先例和經驗,呂提出由對方每年支付費用,讓社會組織托管社區服務中心日常運營。
呂認為,社會組織管理社區的優勢在于會配備較高效的專業團隊,在每年政府固定的購買服務費外,恩派還會將吸納的其他基金會的籌款,用于社區活動的籌辦。
在三林鎮世博家園社區服務中心內,恩派的常駐人員僅5名,而由其引進的社會組織有20多家。在2007年開始,恩派的工作重點只是豐富和完善公共設施項目,而近兩年,呂朝發現,公共設施作為一個公共空間,起到把人聚集,重建社區關系的作用,“要利用好公共空間這個載體。”
呂朝認為,越是人員構成復雜、問題突出的社區,越是社會組織的試驗田。而城市社區、農村社區、城鄉接合部社區的區別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明顯,“操作下來覺得社區建設的大多數基本問題都是一樣的。”
而今年10月上海市社工委組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,有眾多鎮政府代表和社會組織出席。呂朝回憶,這個會類似于“集體招投標”,已經有一些鎮政府表示感興趣。(王丹陽)